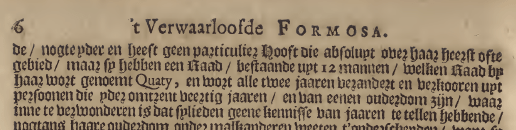書名:地名的野生思考
- 作者:翁佳音、鄭碩
- 主編:何義麟
-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
- 2025年8月
-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介紹頁面
翁佳音老師在 Facebook 發表的非正式連載「地名的野生思考」,終於在學弟鄭碩的協助下整理出版。大概在2018年,貓還在南港獅形當翰林院行走時,就已經有整理出版的想法,但做到一半還是沒有下文。這是台史所703研究室的常態,習慣就好。
《地名的野生思考》是一本略讀起來輕鬆,但精讀起來簡直要學者開 seminar 的書。因為要跟上翁佳音老師的資料量和思考邏輯,自己也必須有相應的實力。這些實力包括史料、語言、地理、民俗知識等知識,還有將上述知識互相串聯互證的思考邏輯。實力不足的讀者可能會誤讀其論述或是把翁老師當神拜,這都不是他期待的讀者。
其實翁老師更在意的,應該是自己的想法和文章沒有人讀吧。以前許雪姬老師溫柔地罵過,翁老師愛在 Facebook 發表,就只圖一個「讚」,不好好將研究寫成論文。可是與其當個拼命發論文積點數的學者,翁老師應該更想當個與公眾對話的知識分子吧。
但《地名的野生思考》由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出版,就會一定是本很難賣的書。不是因為沒有讀者,而是缺了出版者與讀者之間的環節。稍微搜尋一下各大書店就知道了,這本書既沒報品也沒上架,不到新書發表會現場是買不到的。
因此,作為一位比老師還早離開南港獅形,出門亂走迷路到府城,很久沒幫翁老師做事的小貓貓,能做的事就是充當出版者與讀者之間的環節吧。雖然是以廖添丁的形式,但貓相信沒有人會生氣。那就做吧。
📗翁佳音、鄭碩,《地名的野生思考》(臺北: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,2025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