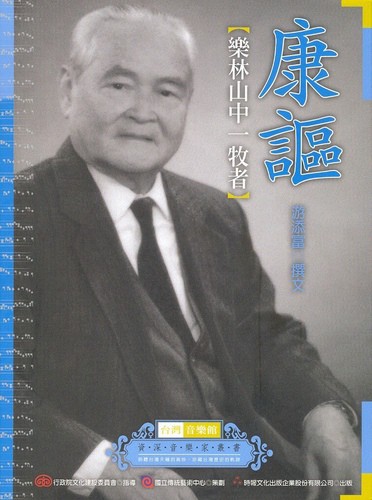太陽花學運已經過去十一年了。或許你不同意「太陽花」或是「學運」,或兩者都反對,但大家都這樣叫慣了。就像我們知道中華民國=台灣=中華台北,雖不滿意,但我們都習慣這樣的日常。算算中華民國統治台灣都八十年了,太陽花學運還不是很久以前的事,甚至可以攏統地算「十年」吧。但從個人的尺度來看,十年也足夠天翻地覆了。
十年過去,世界上對「生活方式」的看法更加兩極化,而我也從歷史的旁觀者變成傳授者,很難繼續保持距離。作為大學歷史系的助理教授,在2024至2025這學年負責學士班必修台灣史課程。我知道他們在國高中已經上過台灣史,甚至感到厭煩,可能還認為這是民進黨政府洗腦人民的工具。我也假定,六七十位修課學生中,大概有三分之二在二十歲時,會將他們的選票投給民眾黨,作為對慘澹青春的復仇。我這個世代的台派會批評這些大學生「民主富二代」,但這種缺乏同理心的批評,只會把他們推得更遠。
在課堂上教台灣史,就像讓自己成為官方認可價值的象徵,必須承受學生真真實實的抗拒。特別是今年四月以後,政府與在野黨的衝突從立法院擴散到街頭的罷免第二階段連署,每週的上課內容,都會與當時發生的政治新聞產生共鳴。雖然我盡量在上課時避免使用煽動性的語言以保持中立,但台灣史作為當代主流價值的化身之一,本來就不可能中立。整個學期我都在想:過去十年,我們到底怎麼了?為什麼在號稱天然獨的太陽花田中,長出了茂盛的草與蔥?
民主的建立與惡性循環
歷史學對社會的意義之一,是透過研究過去,理解現在面臨的情況如何演變而來,而這正好也是今年四月以後我講授的主題。透過回顧歷次修憲內容,我們討論現在台灣的民主體制怎麼建立,如何透過一次次的選舉、罷免、創制、複決,成為我們熟悉的日常和步調。對於民主的實踐,這學期的課本之一《戰後台灣政治史: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》,作者若林正丈有以下評論:
臺灣民主體制的課題,可以說是該如何避免一種惡性循環,亦即該如何避免因挾議會多數、未做政策辯論便對政權進行杯葛阻撓,或主流媒體對陳水扁所做的片面批判,以及臺灣民族主義的動員對抗而加深的彼此不信賴。就目前來講,政治家們在緊要關頭的自我節制、司法領域消解政治過程中無法處理之難題,甚至是社會在達到一定經濟發展後基本安定的自然煞車機制,可以說是奏效的。
在2025年回顧這段在2008年出版的評論,實在不知道當年若林教授是客氣還是樂觀,亦或是現實比想像更離奇。台灣在2024年選出的立法院,微弱過半的在野黨不只濫用議事規則迴避實質的政策討論,甚至讓憲法法庭因缺額無法運作,以致在2025年要由公民發起大罷免來解救束手無策的政府,但最後以徹底失敗告終。
對立的青鳥與小草
在2025年發起大罷免的「青鳥」,經常被媒體描繪成中壯年世代。他們在十年前因太陽花運動而有政治啟蒙的經驗,十年後成家立業,要為下一代保留更好的台灣而努力。當在野黨指控他們「拿錢辦事」,他們常見的反應是「民進黨根本請不起我」,不只強調自發性,也強調他們的經濟能力。在這場運動中,媒體也強調女性的角色,民視《台灣演義》甚至為此做了「女力救台灣」專題報導。
在媒體呈現上與青鳥對立的群體,則是稱為「小草」的民眾黨支持者,他們通常被描繪成二十幾歲的年輕理工科男性,自比為「黨外」,致力於反對「綠共」的「威權」、「戒嚴」、「綠色恐怖」。從台灣史研究者的立場來看,他們願意從台灣歷史擷取反對執政黨的靈感,似乎表示近年的歷史教育還在他們心中留下點痕跡。但我還是覺得奇怪,他們怎麼把台灣史讀成這副德性?為什麼這一個生長於二十一世紀民主台灣的世代,他們的歷史實踐變成戲仿,公民意識也養成得如此奇怪,竟會相信用「理性、科學、務實」的口號包裝的傲慢與獨斷,為以失言而聞名的「阿伯」義無反顧拼一次?
許多人都在尋找原因,也有很多人提出可能的答案。我覺得,既然這些小草都還年輕,在學校學習的經驗仍然在他們的人生中占有重要分量。或許,我們應該往學校找答案。
學校教育:人生的國家政治初體驗
現代人從出生以來,國家與政府就無孔不入地將一個新生命放進既定的框架,以便管理。登記在戶政機關的包括姓名、性別、親屬關係等等個人資訊,決定未來你在社會中的角色。然後政府再給你一組難記的身分證字號,讓你一輩子都跑不出政府的掌握。幸運的是,這些聽起來很沉重的過程,通常都在我們還沒有記憶時就已經完成。當我們長大懂事以後,最會影響到青少年自身的國家政治,其實就是幾乎每個人都會接受的學校教育。看看那〈強迫入學條例〉,你還沒有不讀書的選項呢。
正因為現在幾乎所有人都上過學,當過學生,我們尋找公民意識發展的問題時,就必須觀察不同世代的學生在學期間,國家政治曾經給他們什麼樣的影響,使他們受教育的經驗與先前的世代有何不同。而1990年代以後的台灣,國家對學校最大的影響,無疑就是大大小小的教育改革。從為減輕升學壓力而廣設高中大學、語文與社會領域大幅增加台灣中心的內容,到近年上路的108課綱與學習歷程檔案,這些都是政治,而學生就是直接受到政治影響的群體。雖然被影響的學生不見得有能力指出學校教育背後的政治運作邏輯,但學校教育就是學生的生活重心,必然也是他們在未成年時期認識、體驗真實國家政治的主要管道。
對現在二十幾歲到剛入大學的世代,也就是大約2000年以後出生的人,他們在學校經驗到的政治,就是讓他們最不安的教育改革,特別是會影響他們未來人生的課程綱要和升學制度。這個世代在學校使用的是一綱多本的教科書,升學要參加會考、學測、指考或分科。而他們的家長大約出生在1970年代,使用的是國立編譯館統一發行的教科書,經歷過的則是每年夏天的高中職五專和大專聯考。他們不一定是升學主義的贏家,但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在屬於他們的升學競爭中勝出。但在這一代學生面臨升學壓力的2010年代,則有「95暫綱」到「108課綱」的轉變。面臨如此重大的教育制度變化,他們也延續比他們稍微年長的那個世代,將自己描述為「白老鼠」,而他們認為主宰這個實驗空間的政府,較多時間由民進黨執政。在這樣的生命經驗下,確實不能期待他們認同民進黨政府揭櫫的主流價值。而在他們的政治觀念於成人初期定形後,未來又將造成以世代為規模的影響。
年輕世代的政治態度
要怎麼描述這群2000年以後出生世代的政治態度?他們出生在總統和國會都已經直選的台灣,長大後不再需要對抗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體制,體罰和髮禁都成為過往雲煙,民主與自由對他們如空氣一般自然。但正如前文所述,他們透過學校教育體驗到的政治,以及教育所傳達,被政府設定,老師傳達的主流價值,卻不一定能被他們內化。他們更常見的態度是對變化的焦慮和反感,所以他們特別討厭在同學中的異見人士,或是熱衷於社會議題的倡議者,因為這些都是破壞平穩日常的潛在威脅。
他們也在學校感受到大人主導教育體制的兩面手法。以強調素養的108課綱來說,課綱在理想上彷彿要每個學生都當大賢者,但他們只是忙於應付升學制度中種種要求的學生,不知道大人要怎麼衡量課綱所要求的素養。在面臨升學考試時,所有的素養又被化約成會考、學測、分科考試的成績。雖然考試成績不像聯考時代是決定升學的唯一因素,但仍然是相當重要的因素。用補教界對學測和個人申請的描述,就是看學測成績的「第一階段拼命上」,比較看個人表現和特質的「第二階段不要掉」。雖然現在升大學的評量方式已經比過去多元許多,實際上也是學生挑學系,而非學系挑學生,但重點是學生走過這段歷程的經驗,以及從經驗中得出對國家政治的看法。這個看法,很可能是「大人說一套做一套」。因為教育改革一路以來從降低升學壓力到強調素養,看起來是為他們好,但最後大家還是得考試。這點從聯考世代到108課綱世代,都不曾改變。
在學校教育中體驗到「大人說一套做一套」,會讓學生產生抗拒學校主流價值的態度。小熊英二對1968年日本學生運動世代的研究發現,這些出生於1950年前後的日本戰後嬰兒潮世代,在小學受到戰後民主主義自由教育的洗禮,卻在升上中學以後面臨升學主義的競爭,還有學校為提升學力實施的嚴格管理。在他們生命過程中,不同學習階段老師的態度轉變與落差,讓他們感覺「大人說一套做一套」,因此對大人主導的體制怒火中燒,然後在1968年的不同契機下,組成反抗體制的學生運動。
我不會把2020年代台灣年輕人的政治態度等同於1968年的日本學生運動世代,因為他們追求的目標完全相反,但共同的機制是反抗學校所傳達的主流價值。因此,我們必須進一步分析這個主流價值到底是什麼。以下,我會討論「進步政治」和「台灣民族主義」,兩者都讓他們對現在與未來感到不安。如果以性別區分,年輕男性會覺得這兩個議題都對他們不利,而對年輕女性來說,「台灣民族主義」會是更切身的議題。
令人焦慮的進步政治
說到台灣的進步政治,或許很多人會直接想到2019年通過的同性婚姻,但我認為2004年制訂的〈性別平等教育法〉才是應該探討的議題。〈性別平等教育法〉定義了推動性別平等的學習環境與課程教學,實施二十年以來,被認為有助於下一個世代尊重性別特質,在個人發展上突破性別框架,基本上有正面的評價。但在性別平等教育的實踐中,男女兩性的體驗卻相當不同,甚至令人懷疑接受性別平等教育的世代,是否真的有內化性別平等的價值觀。
性別平等的教育對象並不區分性別,但在實踐中,卻經常還是以二元性別來劃分。結果,在性別平等教育中,女性是被賦權的角色,男性則預設為被防範的角色。若是真正實踐性別平等,兩性都應該被賦權,都應該被防範,不應該有區別,但大家都知道現實不是這樣。在一張防範跟蹤騷擾的宣導圖片中,被騷擾的人物剪影穿著裙子,明確用性別區分加害者和受害者。年輕人常見的俗語「人帥真好,人醜性騷擾」,也反映男性在社會中被當成加害者的預設身分。在這樣的情緒下,年輕男性會感覺性別平等的理念並非真平等,而是對他們的打壓。優勢者的怨言,過去受壓迫族群爭取權利的過程中已經看過很多案例,一點也不奇怪。
性別平等教育的目標,也是對傳統陽剛氣質的挑戰,威脅到2000年以後出生世代男性接過社會主導權的機會。雖然性別平等教育要讓大家不再被父權架構給掌握,但大家似乎忙了一圈,父權體制還是頑強地在社會中找到傳人。具體來說,年輕男性發現在學業表現和就業選擇上,同世代女性都是強大的對手,甚至有機會從上個世代獲取父權紅利,讓他們又忌妒又憤怒。從過去的經驗來看,他們這個世代的男性還沒有看到同世代女性在事業上的天花板,以及為家庭放棄事業的決斷。從性別平等的價值來看,我也不希望現在的年輕女性在未來十年的人生中,再次遇到他們父母輩曾經歷的性別不公。但對年輕男性來說,他們現在還沒看到。如果年輕女性未來真有機會擺脫性別框架的限制,與他們同世代的男性大概也不會拍手鼓掌吧。
結果,雖然年輕男女都面臨未知與不安,但女性好像比較有希望,男性的前途則沒有那麼光明。
堅定的認同卻沒有安穩的未來
對台灣的年輕男性來說,還有更令他們焦慮的未來,就是中國對台灣的持續威脅。從新聞報導和政治制度,36歲以下的男性都是後備軍人,不時要面臨教育召集。2005年以後出生的男性,則要面臨從四個月延長至一年的兵役。或許過去的世代會將當兵視為陽剛氣質的展現,但戰爭的陰影更加巨大。他們愛國,他們愛台灣,但他們想用別的方法來愛。
曾經有外國人無法理解為什麼台積電的勞動條件不好,台灣人還願意為它賣命。有人回答,為台積電工作不只有財務上的回報,也是一種愛國表現。如果將台積電擴大到知名廠商的供應鏈,甚至整個電子業,也是行得通的。我們現在對電子業工程師的印象還是以男性為主的工作,對年輕男性來說,電子業工程師也是被認為有光明前景的工作。如果他們有機會,或許他們會選擇去電子業當研發替代役,而不是在軍營操演武器。
但在他們眼中,民進黨政府的國防政策,可以化約為「抗中保台」的口號,卻會讓年輕男性對未來更加焦慮。他們不只焦慮人生,也焦慮戰爭。如果在戰爭中犧牲,陽剛氣質的榮譽也只是追晉的勳章,對自己一點意義也沒有。他們才不要這樣的台灣民族主義。
對主流價值的抗拒和顛覆
進步政治和台灣民族主義,在二十一世紀台灣都已經是政府透過學校教育傳遞的主流價值。正如前文所分析,年輕男性感覺自己是進步政治的受害者,戰爭威脅則不分性別壟罩在所有人頭上。這讓他們覺得政府和執政黨疏離自己,不再重視他們的聲音。這些自認為被排斥的人已經形成群體連帶感,將自己定義為政府與學校主流價值的對立面,然後把微觀與巨觀的不滿都投射在政府之上。像是用「綠共」、「塔綠班」嘲諷國防政策,用「用愛發電」嘲諷能源政策,用「戒嚴」來嘲諷對政治人物不當行為的偵訊和調查。如果你問他們國防安全、能源穩定、追訴犯罪是否重要,他們應該也會說很重要,但不是現在這樣的做法。這時,如果有政黨能回應他們的不滿,就有機會爭取到他們的選票,然後就是我們在2025年七月最後一個週末看到的狀況:在野黨的全面勝利。
從執政黨疏離人民,讓他們產生被排斥而產生的連帶感來看,驅動太陽花世代與民眾黨小草的政治動力其實一樣,不同的只是當年的政府是國民黨,現在的政府是民進黨。要分析過去十年我們到底學到什麼教訓,現在可能還太早。從世代的教育與政治經驗來分析他們的政治動向,或許是可行的方法。在分析的過程中,我們可能也會感嘆他們年輕不懂事,但在當下的年輕人看來,反而是我們長成自己曾經討厭的模樣。這自我實現的預言,希臘神話的伊底帕斯早就演給我們看了。
在未來幾個月,我們還會繼續看到在野黨挾國會的微弱多數,以監督政府之名,繼續進行constitutional vandalism。對執政黨來說,這次看似2018年底選舉與公投的失敗,但或許更像2006年那種失去話語權的情勢。若林正丈在2008年出版的《戰後台灣政治史》中曾經評論,自從2004年陳水扁以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贏得總統連任後,深綠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論述日益教條化、僵硬化,造成本土化政策無法深入基層。這正是2008年政黨輪替的背景。二十年過去,我們面臨的不再是愛不愛國的問題,而是公民的政治意識是否能鼓勵政治人物負起責任的問題,而現在執政黨似乎沒有將在野黨勸回正軌的說服力。
作為公民,如果我們在羅馬被汪達爾人掠劫後,放棄千瘡百孔的家園,儘管移民到外國就好,那我們真的可以買雞排奶茶旁觀享受這場暴力的盛宴,反正不用負責。如果你這樣就好,那我也這樣就好。